
祝逸雯
2021年4月1日,我在细雨中乘坐高铁,从上海到苏州玄妙观,参加荷兰道教研究专家施舟人教授(Professor Kristofer Schipper,“六七升度功德道场”于1934-2021年举行。
按照中国传统,人死后七七四十九天,灵魂依然徘徊在人间。因此,每隔七天,人们就会为死者举行宗教仪式,为他积累功德。四月一日是施舟人教授仙逝六周的日子,也就是第六个“七”天。范华,施舟人的学生,法国人类学家(Patirce Fava)在倡议下,苏州常熟的道士为施舟人教授举行了道场,邀请了两位道教尊神——太乙救苦天尊和斗奶元君,引导死者超越天界。
道士们在殿外张贴《榜文》
天界榜文
当我走进神秘的斗奶殿时,我看到道士们正在装饰坛场和经台。近门祭桌上有苹果、香蕉、橘子、蔬菜、黄酒等供品,烛光摇曳,烟雾缭绕。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六尺大小的施舟人画像挂在祭桌后面。这幅画像是由国内宗教画家、道教皈依弟子王敏源制作的。画中的施舟人穿着玄黄色的道袍,戴着道冠,手里拿着水板,坐在沙发上。香炉、如意和一套线装本《道体论》放在一边的几个案例上。他身后的屏幕上画着“罗江大霍洞台图”。虽然整幅画像的风格完全是中国式的,但戴眼镜的施舟人的外国面孔仍然清晰可辨。
道服肖像施舟人
近40名国内外学者和教界人士为仪式捐赠了功德金,其中10多人出席了仪式。从下午3点到凌晨2点,法会一直持续到帽日。十几位道士共同为施舟人教授唱诵多部道经,积累功德,召请施舟人之灵到法会现场接受祭祀,最终送亡生天。值得一提的是,与普通人的法会相比,仪式节省了“十王简”的科仪(ritual of audience of Ten Kings of the hell),由于普通人的灵魂在死前,要在十殿阎王那里清算罪恶,而施舟人则是一位受过磨难的道士,不必经过十殿。

道士们跪着背诵经典
这并不是中国唯一一个纪念施舟人教授的道场。3月11日(即“三七”),福建省宁德市霍童山鹤林宫为施舟人举办了“迁神升虚道场”,为他补了道职。
4月7日,中国道教协会还与江西龙虎山天师府、北京东岳庙、上海城隍庙、四川青城山天师洞、福州裴仙宫等五座道观合作,为施舟人举行了法会。
为什么中国道教界如此隆重地为荷兰人举行这些仪式?
石舟仁教授出生于瑞典,祖籍荷兰,祖父是收藏家。他从小就对中国艺术感兴趣。之后,他去巴黎学习,并从著名汉学家康德谟开始(Max Kaltenmar),研究道教史。从沙湾(Edouard Chavannes)算起来,他是读道藏的第四代汉学家。
受益于法国汉学传统的培养,精通八国语言的施舟仁教授非常重视对经典的研究。他花了25年时间带领学生研究明代道藏,重新分类、研究、切断1500多个部门,撰写总结。这个伟大的研究项目最终以三卷书《道藏通考》结束(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Daozang)出版的形式,已成为道教研究人员必备的参考书。该计划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道教研究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是欧美汉学界的著名人士,比如法国远东学院的傅飞岚教授(Professor Franciscus Verellen ),香港中文大学劳格文教授(Professor John Lagerwey)。

需要注意的是,人们的学术治疗与欧洲传统汉学有明显的不同。196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施舟人前往台湾找到了“活的”教学。他崇拜当地高道,施舟道教,学习闽南方言和科学仪器。从那以后,他多次参加当地的盛大仪式,拿起朝板和锣,与道教一起做朝圣和祭坛演奏,并亲自参与道教科学仪器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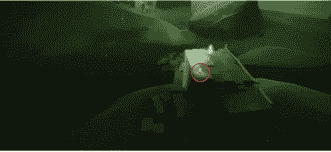
1967年,在台南天坛,移居台湾省的第63代天师张恩溥被授予“正一三五都功经”的职位,并被授予法名“鼎清”。这意味着施舟人在中国道教天庭有自己的地位;作为天人中介,他可以通过道教科学仪器向天庭传达人们的愿望。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高万桑教授是他的学生(Vincent Goossaert)回忆起,施舟人在他的婚礼上穿上法衣,为他举行了祈福仪式。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另一名学生丁荷生教授(Kenneth Dean)满月时,施舟人按照道教传统,通过道教仪式,将女儿的名字报上天庭,从此受到神灵的保佑。
施舟人及其师兄陈荣盛道长
施舟人曾在一次采访中说,学道教,不能从外面进去,一定要自己进去,“道”需要自己去做。施舟人有时会讽刺那些不了解中国民间,不做田野调查的传统汉学家。他在台湾学习了八年,发现了台湾道教仪式的传统,观察了道教仪式与当地寺庙的关系,研究了当地寺庙的水平,描述了道教在当地和帝国的双重作用,激励了许多中国研究人员重新审视当地道教及其与中国当地社会的关系。
2001年,施舟人被聘为福州大学特聘教授,并在中国定居。2003年,他在福州大学世界文明研究中心建立了“西观藏书楼”,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收藏西方文化经典为主的西方图书馆。施舟人于2005年获得了他的中国身份证。自2008年以来,他与国家汉办合作,希望将中国的五经翻译成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12种语言。2013年,他和妻子设立了“爱山”道教名山环境保护研究项目,研究道教名山及其在多元化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在他的画像中,屏幕上描绘的霍童山是他们研究的第一个案例。
我和施舟人在香港有过几次面对面的关系。2008年,他第一次见到他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李志添教授的邀请下,接受了我的博士导师和李志添教授的邀请,为公众举办了公开讲座。因为他的The Taoist Body是我买的第一本西文道教研究书。我看到他小心翼翼地递上书,就像遇见偶像一样。他问了我的名字和写作方法,微笑着签上了“道法自然”和我的名字。
当时我还没有进入道教研究之门。随着我个人研究的发展,他的治学方法——同时重视道经研究和实地调查,对我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事实上,无论研究哪个朝代的道教发展,都不能绕过他的开创性研究,他的论文都是必读的。此外,他对当地文化的关注、道教与中国当地社会的关系也指导了我对上海当地道教和民间信仰的研究。
施舟人第一次来台湾省时,用的中文名是“施博尔”,也就是Schipper的音译。他认为他的祖先可能从事“ship“相关行业,所以取了“施舟人”这个名字。这种不经意间的改名,在今天看来有着美好的寓意。因为在中文中,“船人”就是“渡人”,施舟人为中国道教和道教研究界做出了巨大贡献,确实有“渡人”的功德。
施舟人在荷兰的葬礼上,请柬上印着一句取自庄子的话:“死为昼夜。而且我和子观化和我在一起,我为什么要恶?”这是施舟人在中国获得的一个全新的“自我”。欧亚大陆另一端举行的这些道场,是中国对他最好的尊重和纪念。
注:本文英文版首发于Sixth Tone,原标题为:The Divine Legacy of a Dutch Taoist,在翻译过程中有一定的调整。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道教研究学者朱逸雯。
编辑:韩少华

网友评论